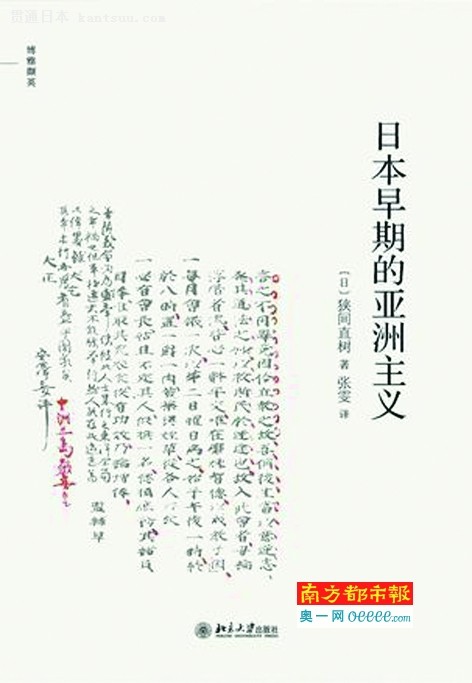|
《绝对欲望,绝对奇异:日本帝国主义的生生死死,1895- 1945》,(美)马克弟著,朱新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2月版。
延伸阅读 《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日)狭间直树著,张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版,59 .00元。 王绍贝 自由撰稿人,汕头 时至今日,部分日本人对于日本如何在短短几十年崛起成为世界强国,依然停留在美化明治维新改革精神上,认为日本人是通过努力学习西方,用自己的奋斗和血汗成就的。类似司马辽太郎《坂上之云》那样切割明治维新与昭和时代,认为明治时代发动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是与此后昭和时代太平洋战争、侵华战争性质不同的正义战争,于是日本向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学习,像他们一样为了自己的“生命线”侵略亚洲邻国,也并无不妥了。马克弟《绝对欲望,绝对奇异》一书正是对这种论调的有力批判,他运用马克思理论及福柯“生命政治”思想,对日本帝国崛起的原因做了深刻的剖析。 福柯关于生命政治的著名演讲———“使人活、让人死”。“让人死”不是说要去杀戮,而是类于“顺从自生自灭的内在趋势”。尽管“使人活”有时候不得不进行杀戮,“让人死”强调的是生命政治的不经意的冷漠。日本帝国的崛起完全符合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 欲望,伴随着中国北方人“闯关东”的壮志,驱动了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之一。1890年至1940年间约有2500万人从山东和河北地区迁往东北。铁路是驱动东北大发展的关键,而修筑铁路需要大量的苦力,只有中国苦力才能“把工人牢牢地固定在生产机器上,按需发配”。日本政府骑在廉价劳工的脊背上铸造了日本的亚洲帝国之梦。记者安达金之助说:“历史上没有一个种族能够在追逐物质欲望的坚韧和毅力方面胜过中国人。”“中国苦力拥有依靠廉价、劣质食物生活下去的能力——— 这些食物在其他地方是用来喂牲畜的……随着东亚生活费用日渐上涨,满洲苦力仍可以靠每天几分钱的报酬生活下去。”直至1860年,马克思使用“中国人的工资”一词来形容世界上报酬最少、受压迫最深的工人群体。20世纪一二十年代,几乎所有日本人关于中国劳工的叙述都展现了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统治”。《满洲日日新闻》报道,有一艘搭载3000名中国苦力往日本工作的蒸汽船沉没,只有8人幸存;时常有苦力忍受不了疲劳工作而自杀;或者被日本流氓残忍杀害;或者因吸毒过量而死。当日本的右翼人士“义正词严”地说日本二战在东北的投资是“赤字”时,他们是否想过为伪满洲国付出生命代价的中国苦力? 如果说中国苦力大部分是生活所迫、“自愿”成为日本帝国的牺牲品,那么朝鲜则是被迫成为日本殖民奴役对象的牺牲品。通过殖民统治的无情掠夺,截至1930年,日本总督占有朝鲜大约55%的土地,直接剥夺朝鲜人的土地和劳动。朝鲜输送日本的大米数量高达本国需求的40%,日据时代朝鲜人食物消费量的绝对减少导致朝鲜人平均身高降低,朝鲜人的工资大幅缩水,而许多日本企业的利润率高达30%-40%。日本殖民者同样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们要应对此起彼伏的抗日运动,“被殖民者只能在暴力行动中、并且只能用暴力的手段才能争取汽油”,“新生的种子,必须在移民腐烂的尸体上萌芽”。 生命政治的另一个重要渠道是卖春。日本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福泽谕吉公开鼓励贫苦的日本女性移民到亚洲各个通商口岸做妓女,用来挣取外汇。日本小说家二叶亭四迷在哈尔滨曾经准备开一家妓院,他认为:日本性工作者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扩张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对俄国人和中国人的色情蛊惑力会使男性顾客很快日本化,然后开始购买日本商品,参与买卖妇女是“爱国责任”的表现,以实际行动支持日本帝国梦的实现。贫穷、不识字的日本女性不可能自己找到在哈尔滨、满洲或新加坡等地的妓院,二叶亭四迷和福泽谕吉的“日本妇女就业论”无疑认可了皮条客在其中扮演的角色。20世纪头10年的3万-5万名在海外从业的日本妓女全部都经过皮条客之手运作。许多流氓都想大赚一笔,然后成为好人;不干小偷小摸,转而做正经生意。贩卖妇女正是“最后一次犯罪”,是一种必要的罪恶,这种罪恶最终会带来善报:原来的强奸犯和人贩子将自我救赎,成为日本国民的模范,日本将从中国人手里抢到利润丰厚的亚洲市场份额,一个富强的大日本帝国即将诞生。 支撑日本帝国梦的另一项生命政治是伪满洲帝国的毒品贸易。伪满大约50%-55%的利润来源于毒品生意,到1944年为止,伪满统治下的4000万中国人当中,有20%染上了严重的毒瘾。鸦片收益为日本军队发动军事行动提供了经济上的保证,日本大正等制药公司在战争时期发展迅速,为欧洲军队持续提供吗啡和海洛因制品。“九一八事变”前,哈尔滨、吉林和奉天“到处是贩毒者,整个城市被毒品弄得乌烟瘴气”。这种状况催生了新的死亡政治管理制度,比如奉天的南门消费区出现了鲜为人知的“土坑”,该城每年死亡的4000名中国吸毒者中许多人的尸体就遗弃在了那儿。吸毒者的身体如果虚弱得无法走出鸦片馆,日本人就会拉着绳子直接把他们扔到“土坑”。 罗莎·卢森堡说:“暴力是资本的永恒武器。”一语道破资本主义的伪自然化面目,正呼应了马克思在《资本论》所写的话:“一面是财富的积累……一面是惨剧的积累,劳动、奴役、残暴和道德堕落。”他强调资本主义体系的存在完全是基于剥削大量工人的生命。倘若没有中国苦力的劳动,没有马克思所说的可怜的“中国工资”,自1905年开始的日本殖民地也就根本建立不起来。倘若没有20世纪80年代起10万日本性工作者(包括慰安妇)和活跃于东亚地区的人贩子(以及在亚太地区各地工作的100万日本人)寄回本土的侨汇,那么日本这些地区根本没法承担帝国主义发展的费用———学校、医院、议会、警察局等。倘若没有剥削这些及其他生命政治劳动主体的隐形剩余价值,那么日本资本没办法进入下一个更高级的形态。 |
日本帝国崛起的“生命政治学”
文化录入:贯通日本语 责任编辑:贯通日本语
相关文章
日本文乐迎来第二位“四代目”人形遣い桐竹勘十郎
京都设计师推出可持续和服,使用回收丝绸和植物染料
歌舞伎团体“新世代”启动全球巡演,融合现代音乐和传统表演
日本文化厅启动传统工艺数字保护计划
日本樱花季延长引发热议
日本茶道复兴吸引年轻人
日本骑车须在机动车道左侧骑行
日本人口不断减少,女多男少,老龄化严重,真实情况令人担忧
日本一寺庙,金碧辉煌,被誉为“土豪”
日本96岁尼姑,整天吃肉喝酒沉溺男色,彪悍人生不需要过多解释
日本的贫富差距为何这么小?
大阪万博纪念公园“红叶节”开幕 红叶与日式庭院交相辉映
草间弥生作品亮相“四叶草”
日本西友、丸井们是如何对待自有品牌的?
日本西友、丸井们是如何对待自有品牌的?
一本书了解日本人眼中的“私摄影”
38条冷知识,让你更加了解日本
日本唯一存活1442年公司,从隋朝到现在,只做一种偏门业务,依然强大
为什么日本的出租车上偶尔会看到“SOS”?
为什么日本工薪阶层也能住独栋“洋楼”?
96岁的日本尼姑吃肉饮酒,沉迷男色,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处女率超高的日本,真是一个低欲望的社会?
经济高增长,日本女性为何回家做主妇?
日本人是如何保持健康的?4个“小秘诀”多学习,或帮助身体长寿
为何日本性同意年龄只有1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