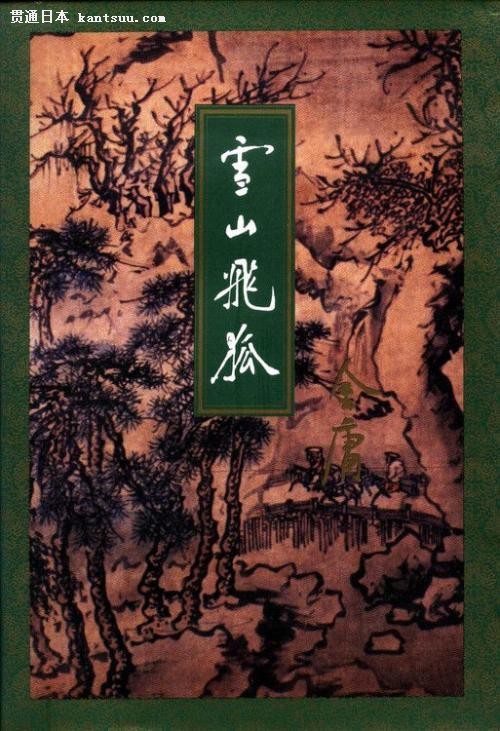|
《雪山飞狐》(图源于网络) 2003年,金庸为《雪山飞狐·后记》补写了几段。其中谈到:“报上还没发表完,香港就有很多读者写信问我:是不是模仿电影《罗生门》?这样说的人中,甚至有一位很有学问的我的好朋友。我有点生气,只简单地回覆:请读中国的《三言二拍》,请读外国的《天方夜谭》,请读基督教圣经《旧约·列王纪上·一六-二八》,请读日本芥川龙之介小说原作《罗生门》的中文译本……”1959年给朋友写信时,金庸“有点生气”。四十几年后写出这节文字时的金庸,犹有几分愤愤之意。 金庸之所以如此“情绪化”,窃以为,主因有二: 一则,这些指认金庸模仿《罗生门》的读者们的见识太过浅陋,完全不明白“自古以来,一切审判、公案、破案的故事,基本结构便是各人说法不同,清官或侦探抽丝剥茧,查明真相,那也是固定结构”,而将其算作了《罗生门》导演黑泽明的首创与专利;如此一来,金庸就成了黑泽明亦步亦趋的学步者与跟风者,显得很有几分“趋时”与可笑,让金庸很是不爽。 二则,我一直感觉,金庸对日本文化日本文学并不如何尊崇重视。 自秦汉到清末,两千年来,中国文化人对日本文化与文学基本就是无视的态度。金庸很传统,继承了这种“上国心态”,对日本文化缺乏敬意。 六十年代的金庸,对日本报业的发展规模表示惊叹,对日本经济恢复之迅也表达过赞佩之意(回看母国的状态,怕是也有几分“妒火中烧”),但他几乎从来没有主动谈起日本文学。 有记者问到了,金庸也跟着谈起过小说《宫本武藏》。他并不像清代以前的国人一样,对日本文学完全无视,好歹还是读过一些的。 中国的“武侠小说”、西方的“骑士文学”与日本的“武士小说”,这三种文体是比较接近的。金庸对西方“骑士文学”和日本“武士小说”的态度却是大异。 写骑士以及深具“骑士精神”的人,写他们建功立业的故事,这样的文学作品,都可算作(广义的)的“骑士文学”。金庸终生视司各特、大仲马为师,多次表达感恩之意。他对日本的“武士小说”恐怕就没这么看重,更多是平视乃至俯视,出于好奇,“随便翻翻”的态度,看看他们怎么写、写些什么。 “新武侠小说”两大家中,古龙受日本小说尤其是日本的“武士小说”影响很大,金庸所受影响很小。 金庸一直爱好周作人先生的文章,但似乎并未受知堂影响而爱好日本文化。钱锺书在小说《猫》中,狠狠嘲弄了知堂老人一把,字里行间也可看出钱先生对日本文化的态度,与金庸很相似,就是不亲近,不重视。 也不仅是钱、金二人,民国时代“欧美派”(或“留欧派”)的知识分子普遍看不起“留日派”,也更不重视日本文化。 不少人参观过金庸的书房,好像没有谁留下了书房中日本著作很多的印象。 金庸对陶杰说过:“我看的英国书多,受那边大学的影响也深,我也喜欢法国、意大利。”他年轻时虽不曾如愿到剑桥读书,思想观念上与“留欧派”很接近的。 金庸的父亲很早就应许儿子,送他到剑桥读书。金庸从小学到大学,成绩几乎总是第一,考剑桥应该没问题的。不得踏上剑桥,还不是让日本人害的!家业因日寇入侵,几乎败光,没钱去留学了。 金庸生平最长的一次对谈,谈话对象居然是一个日本人。那也不见得是他对池田大作有兴趣,我感觉金庸某种程度上是把日本人池田大作看作了英国大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未亡人”。金庸崇拜汤因比,而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对谈录影响深远。汤因比已逝,能与和汤因比长谈过的池田大作谈谈,也是好的。
吉川英治《三国志》(图源于网络) 金庸对池田大作谈到过吉川英治所写《三国志》,更多是他对三国这个时代和《三国演义》这部中国古典小说感兴趣,想看看日本人怎么写、写什么,随便翻翻罢了。 金庸对池田大作又说起:“我家庭本来是相当富裕的,但住宅给日军烧光。母亲和我最亲爱的弟弟都在战争中死亡。”这样亲身经历的家仇国恨,很难让金庸对日本文化有亲近意。(文/刘国重) .. |
金庸与日本文化
文化录入:贯通日本语 责任编辑:贯通日本语
相关文章
日本文乐迎来第二位“四代目”人形遣い桐竹勘十郎
京都设计师推出可持续和服,使用回收丝绸和植物染料
歌舞伎团体“新世代”启动全球巡演,融合现代音乐和传统表演
日本文化厅启动传统工艺数字保护计划
日本樱花季延长引发热议
日本茶道复兴吸引年轻人
日本骑车须在机动车道左侧骑行
日本人口不断减少,女多男少,老龄化严重,真实情况令人担忧
日本一寺庙,金碧辉煌,被誉为“土豪”
日本96岁尼姑,整天吃肉喝酒沉溺男色,彪悍人生不需要过多解释
日本的贫富差距为何这么小?
大阪万博纪念公园“红叶节”开幕 红叶与日式庭院交相辉映
草间弥生作品亮相“四叶草”
日本西友、丸井们是如何对待自有品牌的?
日本西友、丸井们是如何对待自有品牌的?
一本书了解日本人眼中的“私摄影”
38条冷知识,让你更加了解日本
日本唯一存活1442年公司,从隋朝到现在,只做一种偏门业务,依然强大
为什么日本的出租车上偶尔会看到“SOS”?
为什么日本工薪阶层也能住独栋“洋楼”?
96岁的日本尼姑吃肉饮酒,沉迷男色,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处女率超高的日本,真是一个低欲望的社会?
经济高增长,日本女性为何回家做主妇?
日本人是如何保持健康的?4个“小秘诀”多学习,或帮助身体长寿
为何日本性同意年龄只有1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