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印本文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关闭窗口 何谓东洋?何谓西洋?——让日本国民文豪困惑的问题
70多年前,日本唯美大家谷崎润一郎写《阴翳礼赞》一文。说日本阴翳文化是为了遮隐东洋发达的黄色肌肤。谷崎近乎病态地赞美西洋人白色肌肤,丑化东洋人黄色肌肤。作为论述日本文化的这篇近代名作,竟是在从心里赞美西洋,蔑视东洋的基调上成立的。 对此,谷崎宣称,就像木头能接上竹子一样,东洋文明必须接上西洋文明。他成了全体日本人屈辱感的代言人。因此他也成了国民文豪。
谷崎烦恼于和式和洋式之间。西洋的水洗便器便利卫生,但光白陶器泛着冰冷和坚硬的寒气。这样的触感日本人是不习惯的。更为可怕的是自己的排泄物在光亮中被一览无遗,更是令人恶心。而日本传统的和式厕所则用土壁和木板间隔,在暗黑中,建构了一个静谧的冥想空间。上厕之人,会有一种心灵的安逸感。

谷崎润一郎
但是现在这种东洋式的暗黑则让位给了西洋式的明亮,这令谷崎担忧。一边爱用白色陶器的水洗便器,一边不能抑制对和式厕所的怀念;一边赞美西洋女子的白色肌肤,一边以黄色肌肤的松子夫人为最爱。对西洋的憧憬和对日本的乡愁,着实困扰着谷崎润一郎。 这就令人想起日本近代化的三代人物,他们也有着同样的心路历程。
日本近代化第一代人物——
西乡隆盛1827年(文政十年)生。大久保利通1830年(文政十三年)生。福泽谕吉1834年(天保五年)生,大隈重信1838年(天保九年)生。当历史的时钟指向明治元年(1868年)的时候,西乡42岁,大久保39岁,福泽35岁,大隈31岁。第一代人对西洋文明全盘接受,对东洋小岛的土着文化没有太大的感觉。因此也就没有选择的痛苦和乡愁的困扰。多少年后的谷崎润一郎式的憧憬与乡愁,对他们来说近乎天方夜谭。
日本近代化第二代人物——
坪内逍遥1859年(安政六年)生。森鸥外1862年(文久二年)生。当历史的时钟指向明治元年的时候,坪内是10岁。森是7岁。夏目漱石,尾崎红叶,幸田露伴和正冈子规,他们都是1867年(庆应三年)生,第二年的明治元年刚满周岁。第二代知识人迎来了明治的青春时代。这代人懂外语,留过学(如森鸥外和夏目漱石,明治政府出资去欧洲留学。)。面对日本西洋化的浪潮,他们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的疑问。
日本近代化的第三代人——
他们都是明治时代出生的人。永井荷风1879年(明治十二年)生。谷崎润一郎1886年(明治十九年)生。荷风的父亲是文部省和内务省的官僚,也是日本邮船的大官。也就是说,他的父亲是日本近代化推进人之一。但荷风激烈地反抗父亲,在东京躲进文学的世界里,封闭在江户的色欲残香里。谷崎虽然没有像荷风那样的反骨,但他在快乐的享用西洋文明的同时,对日本古来的风土抱有乡愁,却是不争的事实。
三代人的心路历程,指向的是同一个问题:何以为东洋?何以为西洋?

国木田独步
1871年出生的国木田独步,在甲午战争的时候是一位从军记者。战后为了寻求“震惊”的刺激,跑到北海道寻找“新世界”的永住之地。一踏上这块土地,他就叹息:何处是社会?人类可以自豪传颂的历史又在哪里?其实,历史就在他的脚下。他只是不知情,或者假装不知。北海道的空知,历史上是阿伊奴族居住之地。明治维新后,政府开拓北海道。当然并非单纯的“原野”开拓,其中包括了对原住民阿伊奴族的杀戮与同化。
有日本学者将这视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第一步。问题是国木耐不住荒凉与寂寞,不久便又回到了东京。这回来到了当时还什么都不是的武藏野,却无意中发现了灌木丛“风景”。1898年发表日本文学史上的不朽名作《武藏野》。他的笔触这样伸展着:“满以为走那条路可以遇见希望见面的人,可又偏偏不相逢;满以为走这条路可以避开不希望见面的人,可又偏偏会在树林的转角处碰见。”
可见,国木的日本“风景”发现,乃是对无视外界存在一味强调内面优越的一个自立。为什么一定是西洋呢?东洋的风景存在难道就不可思议?他想对日本人意识层中的“鄙视存在”这个意识作个颠倒。这就如同1847年出生的自由民权运动理论家中江兆民,一直用文言体写作,然而他又能将卢梭的《契约论》翻译成汉文。这表明他在面对西洋的时候,也有一个如何自立的问题意识。
1863年出生的冈仓天心,他在1903年发表《东洋的理想》。开篇提到“Asia is one”,即“一个亚洲”或“亚洲一体”的思想。之后虽然被视为是“大东亚共荣圈”理论上的始作俑者,但在其本质上则是对西洋的一个表态。三年后他出版《茶之书》,更是将茶道提升为“亚洲的一个礼仪”,他想用东洋的神秘主义迷惑西洋从而达到抵抗西洋的目的。这确实也起效用了。100多年后的今天,这本《茶之书》在西方仍受欢迎。美国的一些大学至今还用它作为语言科目的教材来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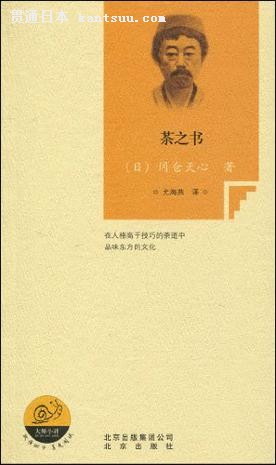
(日) 冈仓天心/尤海燕/北京出版社/2010
1892年出生的芥川龙之介,于1922年在《新小说》杂志上发表《诸神的微笑》。这篇字数不多的小说在思想史上之所以值得关注,就在于小说本身高扬了一个观点,一个处于东洋的我们“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观点。外来的不管什么思想,佛教也好基督教也好儒教也好,在这片土地上都将被改头换面。
芥川在文本里这样得意地描写道:“我们在树木里,在浅浅的水流里,在掠过蔷薇的威风里,在残留于寺院墙壁上的夕阳里。总之,我们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你得当心哟,你得当心哟。”叫谁当心呢?叫被称为“希腊诸神的那个国家的恶魔”当心,因为我们也有“大日灵贵”(天皇家的祖先,天照大神的别名)。

夏目漱石
1867年出生的夏目漱石,在1914年发表小说《心》。通过妻子阿静揶揄的口吻,对丈夫“先生”说出的“受了明治精神影响极深的我们,就是以后活下去,也毕竟是不合时宜的”这句话,“开玩笑”地说:“那就去殉死好啦。”这里漱石用“开玩笑”一词,表现出阿静对武士道的殉死是抱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充满自由,独立,自我的时代,殉死行为是多么的不合时宜与自欺欺人。这里小说的暗示非常有力地指向乃木将军随明治天皇殉死事件。乃木的妻子静子也一起殉死。静子——阿静。乃木——殉死。天皇——陪葬。在这里夏目漱石亮出思虑的配对,显然是指向“东洋意识”与“自我本位”的觉醒。而这个觉醒,则是不依赖西洋的。
因为没有西洋,东洋也将会完成“心”的改造。多少年后,1899年出生的川端康成在《雪国》里,则完成了一种穿越:“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翻译成中文虽然平淡无奇,但日语的“国境の長いトンレルを抜けると雪国であった”语感,则表现出一旦穿过隧道的尽头便是另一个世界。已有妻室的主人公穿过隧道进入另一个世界,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主人公也不知道。这里,川端康成亮出绝对不会遭遇“他者”而照样能创造出“别样世界”的思路,显然不是历史的脉络。或者说得更白一些,历史在这里干脆消失了,剩下的惟有自然,白茫茫的雪国之自然。
显然,从“心”的改造到对“雪国”的穿越,这里一脉相承的依然是东洋的坐标与东洋的原理。 或者用冈仓天心的话说就是亚洲的“蓄水池”或“美术馆”。
1942年(昭和十七年)日本《文学界》召开以“近代的超克”为主题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尽管一直被定调为是“日本帝国侵略扩张”的理论务虚会,但会上提出的一个话题“世界史的哲学”,其潜在的指向就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普遍性”是否还有效?超越普遍性的特殊经验的可能领域,是否能给这个“普遍性”置于相对化的位置?
座谈会为此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东洋“如何对应近代化=西洋化这个图式的变容”(参见大泽真幸《战后的思想空间》,筑摩书房,1999年)。而生于1870年的西田几太郎,在1940年刊行《日本文化的诸问题》一书。书中的一大亮点就是提出了“作为物的皇室”这个命题。这里“物”是个什么概念呢?这里的物并不是广义世界的超越之物,而是在经验世界里,与他物相容相交之际作为特殊的事物被内面化之物。所以西田认为天皇和皇室的超越性,就体现在这个“物”里。
这里的理解难点是:虽有超越性,但并不具普遍性。西田说,这就是天皇制的东洋构造。这就与1914年出生的丸山真男将天皇制视为是一种“空间性的杂居”和“无限拥抱性”有其逻辑上的一致性。这种“空间性的杂居”和“无限拥抱性”丸山又将其称之为神道。那么从关联性来看天皇制也可别名为“神道”,别名为“日本式的东西”(日本的なもの)。而1889年出生,年轻时留学德国的和辻哲郎,也在这种东洋的“宽容性”里发现了“日本式的东西”。他在《佛教思想在日本的移植》中说,日本人的佛教化并没有彻底否定佛教之外因素的那种“回心”,毋宁说日本人也将佛教看作是自身之物。这就是非常精致的排除了西洋因素的东洋论了。
当然论及东洋与西洋,竹内好是跳不过去的。1910年出生的竹内好,通过研究鲁迅向中国“租借精神父亲”,这是他思路出奇的地方。问题是鲁迅精神是什么?现在看来不就是对国民性的解剖与批判吗?而对守旧落后麻木的国民性批判,其目的不就是要引进新学或西学吗?这何来如竹内好所说的鲁迅是“批判近代日本的一个精神参照”?鲁迅在文本里还多次提及要引进日本的思想与文化呢。
竹内好想通过对抵抗、抵制、压制、失败、绝望、奴才等精神历程的再思考再认识,强调日本没有遭遇过这些精神历程。 这种主体性的缺失,使得他在《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一文中得出“换言之,日本什么都不是”的结论。
而“东洋(中国)通过不断抵抗,正在赶上欧洲,超越欧洲,创造出非欧洲的东西。”竹内好的这篇文章写于1948年。时间上是日本战败的第三年,也正好重叠占领军的“外来思想”重新收拾日本意识形态的时节,竹内好可能感受到了什么叫失败、绝望、压制、奴才,所以说出了感受中国的话。但那个时候的中国也正处于“解放战争”(国共内战)之际,能何以看出已经“超越欧洲”?在什么地方“超越欧洲”了?没有人知道。
果然,问题有了转向。1964年,竹内好写《日本人的亚洲观》,其引发争议的“亚洲连带感”这句话就出自其中。他写道:“侵略固然不好,但侵略也从侧面表现出扭曲了的连带感。从某种意义上说,与事不关己放任自流的态度相比,侵略甚至是更健康的表现。”“只是,过分增恨侵略,以至于否定以侵略形式呈现的亚洲连带感,恐怕是将孩子喝洗澡水一起倒掉了吧。这也是因为日本人始终无法从目标丧失感中恢复过来。”这就非常有看点了。
竹内好奇妙的心情转换是从何而来?1964年代,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1964年又是东京奥运会的举行年。无自我,无原理,无坐标,无抵抗的日本,这个经济发展的底气是从何而来的?这些都使得竹内好陷于一种学术尴尬,一种“优等生文化”何以能取得这些成就的尴尬。而在竹内好眼中真正“强者”的中国(或曰“弱者抵抗”的中国)则在那个时节上陷入了某种不可测(1966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面对“日本的进步”,面对即便是放弃原创模仿而来的,但也是一种进步的面前,竹内好是否在作某些学术上的调整?这是否才是提出“连带感”的政治与经济的背景?
竹内好本想在思想史的构造上确立面向现代化的中国的文化模型。但从结果看,还是“优等生”的日本先于中国步入现代化行列,而被竹内好看好的坚决抵抗“西潮”的中国,付出的则是代价与时间。这样来看,竹内好的中国观还仅仅是一种理念,一种假说,一种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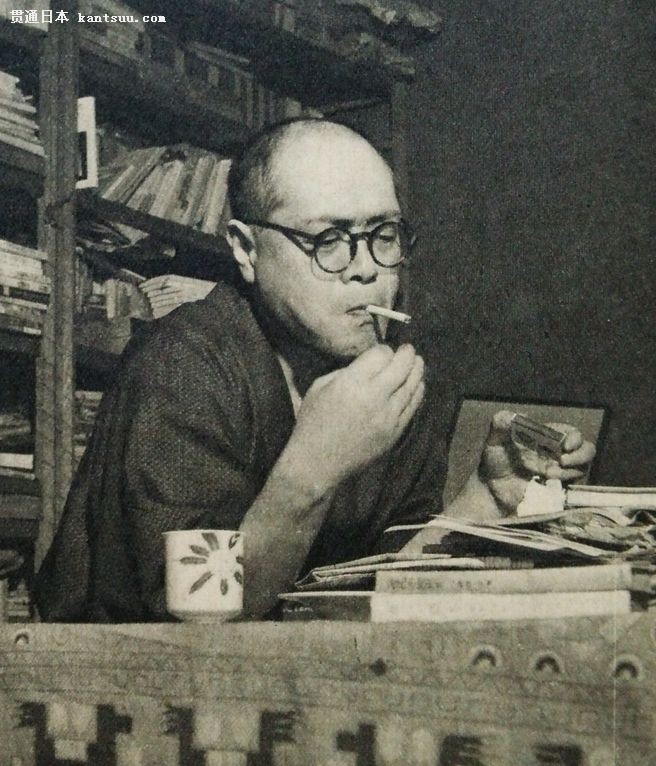
竹内好
不在西洋,也不在日本,而是在中国找寻他心中的“东洋范型”,这种虚构和幻想,充其量也只是脱西洋或反日本的一种思想实验。这样来看盛行多年的中国“日本研究”学界的竹内好热,从某种意义上也只能说是本土情怀的一厢情愿。
1941年出生的评论思想家柄谷行人在《日本精神分析》(讲谈社,2007年)一书中,指出中国文学研究者竹内好则“通过与中国对比来批判日本”,但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日本发展的“秘密”就在于“既没有自我也没有原理”。而这句话的反说就是有了原理性的坐标轴,带来的不是“发展”而是“停滞”。但竹内好的执着在于“他宁愿期待中国式的对原理的执着,那样倒是更接近于西方。”不带偏见的话,这是对竹内好的一个学术嘲讽。
而战后出生的日本知识人则从战争问题着手,探讨何谓东洋何谓西洋。这里注目的是1948年出生的加藤典洋,他在批判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的同时,提出一个问题:我们面临着一个“如何追悼为罪恶的战争而死去的本国国民”这个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课题。实际上这个思考是他在1995年《群像》上连载而成书的《战败后论》的一个逻辑延续。
在这本书里,加藤提出为了向整个亚洲的战争被害者表示哀悼和谢罪,日本人首先需要哀悼日本自己的战死者,通过纠正“人格分裂”将自我统合为一个完整的“国民主体”。那么这个“国民主体”是否就是竹内好所说的具有“自我”意识的“国民主体”?或者如丸山真男所说的具有了“坐标原理”的“国民主体”的呢?
而在1949年出生的村上春树,则在2002年发表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小说恰好也是讲了一个“自闭”的人如何从自己“内侧”找到恢复自我方法的故事。通过“自我的世界”,最后找到“世界中的自我”。这个“世界中的自我”也就是有了东洋元素的自我。前者是在哀悼和谢罪中回归“自我”,后者是在自闭的勃发中找到“自我”。不同的路径通往的是一条大道:如何定位东洋如何定位西洋。
当然,1956年出生的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则批判加藤典洋的回归一个完整的“国民主体”论。他在《战后责任论》一书中认为先“内”后“外”,先“自己”后“他人”,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这种模式只能起到模糊战争记忆,消除战争罪恶的目的,从而使战争责任进一步暧昧化。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另一层面的东洋与西洋的诉求。
在行将结束本文之际,笔者又想起1861年出生的内村鉴三。他在1908年出版《代表的日本人》一书。书中介绍了日本明治前后五位风云人物,即远见卓识的革命家西乡隆盛,爱民如子的封建领主上杉鹰山,勤劳节俭的普通农民二宫尊德,道德高尚的知识人中江藤树和博大精深的宗教者日莲的生平事迹。把他们视为日本人的代表,实际就是在强调勤劳、节俭、忠诚、勇敢、调和这五大精神元素。在这些日本人身上,不仅体现了儒、道、佛的融合,而且还体现了东西方的融合。作为基督徒的内村鉴三,则对孔子表现出恭敬与遵从。他承认孔子是“中国的伟人,东洋的伟人。”实际上,这里的恭敬与遵从也是对西洋反省的一个结果。
“继中国的哲学家们之后,传来的是印度的王子悉达多。”
老人一边继续说着话,一边摘了一朵路边的蔷薇花,高兴地闻着香味。但在蔷薇花被摘的地方,依旧还有着那朵花,像雾一样弥散着。
芥川龙之介的《诸神的微笑》如是说。
 打印本文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