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印本文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关闭窗口 专访东大教授末木文美士:日本人的精神核心是佛教
(原标题:专访东大教授末木文美士:日本人的精神核心是佛教)
东京大学的末木文美士(Sueki Fumihiko)教授多年来专注于日本佛教史与东亚思想史的研究,他的《日本佛教史——思想史的探索》在日本重印二十多次,至今畅销不衰,最近由“复旦文史丛刊”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引进出版。近日,他来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讲演,记者借此机会请他谈谈日本佛教研究的相关情况。

末木文美士教授。澎湃新闻: 为什么您的《日本佛教史》要特别注明是“思想史的探索”,这种探索的特点是什么?与其他的日本佛教史著作相比,您在写法上有什么不同?
末木文美士: 日本佛教史的书写是明治维新后才逐步确立起来的,它从一开始就采用了比较近代的方法,最初是用来记述佛教的传统教理随着时代的推移有何变化,后来逐渐出现了一些史料批判的写法,于是批判型研究逐渐成为主流。但二战后,对批判型研究有了新的认识,开始更多地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来考察和书写日本佛教史。在此背景下,我自己的研究是比较重视佛教的内容:佛教在思索什么,这些思索又对日本文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我在写作《日本佛教史》时所谓的“思想史的探索”。

末木文美士著《日本佛教史——思想史的探索》。澎湃新闻: 您提到过,在日本真正古老的是佛教,神道教是受到外来佛教的冲击才逐渐理论化的,那现在佛教与神道教是什么关系?
末木文美士: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明治时代,神道教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因为引发明治维新的政治力量想运用神道教来实现他们的政治和社会理想,于是他们推动了神佛分离的倾向。由此可见,在这之前,神佛是交杂在一起的。那么神佛分离要如何实现呢?实际上就是把神道中的佛教因素剔除掉,使神道成为独立的宗教体系,并使之完善起来。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强调神道教是日本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宗教信仰,但是由于佛教的掺入,使得神道不那么纯粹了,而神佛分离的目的就是要恢复它古代的纯粹性。这种想法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但随着日本在二战中战败,这种想法就被否定了。二战后,神道教应该如何发展,它应该在现代社会中起到何种作用,这些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思考和讨论。现在有一些神社的神职人员认为,应该恢复明治时代的神道方式,但很多人是持不同意见的,批判这种想法。所以,神道教的发展方向,在日本社会并没有达成共识,也没有经过充分的讨论。
我个人认为,日本传统神道中的诸神,他们有很多优势和好的地方,但是能够充分发挥他们优势和好处的思想还没有建立和健全起来,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后的一种思想任务。
澎湃新闻: 那您如何看待《西游记》这样的文本,其中融合了神、佛、妖等各种元素,日本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民间文学作品?
末木文美士: 民间文学作品非常丰富地体现了民众的信仰,但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儒教被认为是思想的正统,所以过去对这些民间信仰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和评价,今后我们在考察中国思想的时候,对这部分材料要予以充分的理解和关注。
在日本,也有类似的文学作品,比如《平家物语》。它是一部历史文学作品,但它的总体思想是在描述人世间发生的变动——它认为变动的原因在于冥界,是背后的力量使人世间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此外,在中世还有能剧。它的重要特点就是描述在人能看到的世界之外的世界——神的世界、佛的世界、死后的世界等等。这些都是日本人在文学或文艺上表现出的对冥界的思考。

周作人译《平家物语》。澎湃新闻: 日本佛教和中国佛教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如果写中国佛教史,是不是也可以用“思想史”的方法来写?
末木文美士: 我认为,日本人的精神核心是佛教。比如说所有人死后都会在寺院里有一块地方供奉牌位,人的终极归属是在佛土;而佛教对中国人的精神虽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中国思想的核心是儒教,佛教的影响是处在背后的、潜在的、不易被察觉的。
中国也有很多学者从思想史的角度书写了中国佛教史,表现了对思想内容的关切。比如葛兆光教授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时就很重视佛教。当我们考量整个中国思想史时,我觉得有一个方面必须得到重视,那就是儒教与佛教之间的关系。书写中国佛教史,必须关注到佛教对整个思想史的影响和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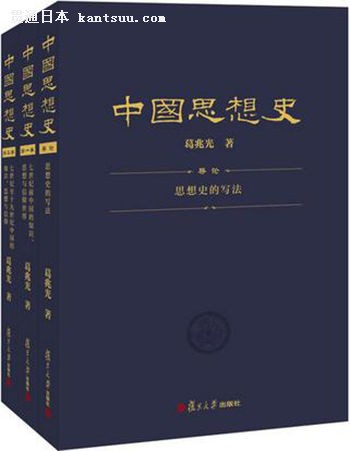
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澎湃新闻: 您在东京大学印度学佛学研究室待过很长时间,是否可以谈谈日本学术界有关佛教研究的传统与特点?
末木文美士: 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佛教研究采取了近代的方法,获得了很大的进展。这个近代的方法,主要来自欧洲的近代文献学。在欧洲自身的学术发展史中,近代文献学是在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中建立起来的一种学术研究方法。他们也把这种方法运用到对古代印度的佛教、哲学和经典的研究中去。而当时很多日本学者是到英国和德国去留学的,因此他们就学到了这种文献学方法,并应用到日本的佛教研究中。欧洲的学者可以读印度的古典文献,但很少有人可以读古代中国的汉文佛教经典,而日本学者可以两者兼读,并对两者进行比较,所以日本学者开拓了一个欧洲学者无法达到的新领域。
当时的日本佛教研究,是以印度为中心的,所以东京帝国大学是将佛教研究放在印度哲学专业之下,而对东亚佛教的研究,包括中国的和日本的,则比较落后。虽然当时完成了校订、出版《大藏经》这样的大工程,但成果主要集中在文献学研究领域,如何解读这些佛典、佛经,思想史领域的研究是很不充分的。
澎湃新闻: 那么在明治维新之前,传统的佛教研究是怎样的?
末木文美士: 明治之前也有一些学者非常重视文献的考据,但具体的做法与欧洲的近代文献学有些不同。当时中国也盛行乾嘉考据之学,日本可能受到了这个影响,也要对汉译佛教经典进行文献研究。
所以,明治之后最大的不同,可能就是开始解读印度梵文和巴利文的佛教经典。因为大家都知道,佛教发源于印度,它的根本在那儿,而传入中国、日本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大家倾力于发现佛教原本是怎样的。但这种倾向引导出了一种消极的结论,即东亚的佛教不是真正的、原来的佛教。
澎湃新闻: 这种消极结论会对日本学界有负面影响吗?
末木文美士: 这使得日本学界无法对汉化佛教和日本化的佛教做出公正的评价。在中国,人们对汉化佛教是持肯定态度和积极评价的。但在日本,当人们讲到佛教的日本化,却认为佛教失去了原来的面目,是它的堕落和劣化。大家都在关心原本的印度佛教究竟是怎样的,而忽视了佛教在日本社会中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因此,研究者在研究一个理想化了的印度佛教,但这个研究对象与日本社会中真实存在的佛教是乖离的、割裂的。于是,我在研究日本佛教史时的一个追求就是要找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即原本的佛教思想源流是怎样的,它进入日本后,为什么发生变化以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对今天的日本有何影响。可以说,我的研究兴趣在于佛教进入日本后的变化、适应和影响。
澎湃新闻: 我们知道,您对明治时代的佛教、哲学与思想有深入的研究,前几年出版了几部著作,恰好这一段时间,也是日本对中国有深刻影响的时期,您能否谈谈日本佛教的新思想是什么,它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末木文美士: 正如前面所讲,明治之后,日本的佛教研究吸收、应用了近代文献学方法,同时,佛教思想也适应了日本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其中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合理化。因为在近代之前,比如佛教中的净土宗宣扬人死后可以往生净土,归得善所,但这个想法在近代思维中是不太能被接受的。于是,它进行了调整,宣称净土就在你的心中。不过,当然了,放到现在,“净土就在你的心中”这个解释也再次受到挑战,需要重新评价和讨论。但无可否认,佛教在明治时代做了近代化的努力和尝试。
而中国可以说是非常积极地吸收了日本佛教近代化的思想。日本有一位佛教哲学家、改革者叫井上円了,他原先非常精通西方哲学,把西方的哲学和自然科学都融入佛教的新思想、新解释,致力于构建佛教哲学。他的很多著作都很快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中国近代革命家章太炎也受到了日本佛教的影响。中国近代佛教改革家太虚大师对日本的佛教近代化趋势也非常关注,而且积极推动中日佛教之间的交流,吸收了很多日本佛教新思想。

井上円了。澎湃新闻: 您主要研究日本佛教,但也调查过现代中国佛教,那么,您能否谈谈“东亚佛教”的综合研究是不是可能?
末木文美士: 因为东亚地区的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都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但三个地方对佛教的接受,以及佛教在当地的具体发展和特点,又是不一样的,存在着差异。那么,相互了解这些异同,不仅有利于加深对佛教的理解,而且有利于三个地方的人们互相加深理解。
我和其他几位研究者有一个合作项目就是《东亚佛教史》,已经完成了写作,稿件正在编辑中。过去对东亚佛教史的写作,一般会将三个地方分开写,以地域为区隔,而我们现在所采取的方式是在同一个时代考察三个地方如何吸收佛教,又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澎湃新闻: 您和中国的佛教研究者接触很多,能否谈谈中国佛教史研究中应当注意的问题,能否评价一下近年来中国佛教研究的情况?
末木文美士: 我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与中国的佛教研究者接触变多的。因为在此之前,可能受到“文革”的影响,中国的佛教研究者本身就不是很多。近年来,研究人数在增多,而且年轻学者变多了,这都是非常好的趋势。
但我也有担心的地方。比我年长的、“文革”前就开始佛教研究的学者,或者跟我同年代的学者比如葛兆光教授,虽然他们的人数不是很多,但他们都有一个很宽阔的研究视野,试图在研究中把握全景和全貌、抓住大的脉络。而现在的年轻学者,人数是变多了,但他们把研究范围变得比较小,可能是希望在限定的领域中更快地拿出更多的成果。所以,我感觉,这使得最近的研究成果对整体的把握不像以前那么充分。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日本也有这样的问题。
澎湃新闻: 这会不会是因为年轻学者认为深入的细部研究也很重要,您如何看待整体把握与细部研究之间的关系?
末木文美士: 对细节进行深入研究,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但我现在担心的是,这些细节的研究是在接受既有的整体理解下展开的。举例来说,佛教有各种各样的宗派,但这些宗派原先是没有的,到江户时代后才逐渐产生,宗派的门户也逐步建立起来,而且彼此之间越来越泾渭分明。日本的宗派思想也对中国产生了影响,中国也接受了各个宗。那么,现在的研究如果都以这些宗的构造为前提的话,就不能突破各个宗之间割裂的局面。这些细节研究是无法对整体理解提出质疑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真正理解佛教的整体变化,恐怕要突破这个前提。细节的研究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对整体的构想和把握,恐怕只能在小范围内打转,它的前景是有限的。
澎湃新闻: 现在,专门的学术类著作,在日本也好,在中国也好,读者都不多,但是社会上对通俗简明的知识类读物很需要,我们听说您除了专门的学术著作之外,还写过不少有关佛教和思想、文化的“文库本”读物,您能谈一下写作这样的通俗知识读本的经验和意义吗?
末木文美士: 的确,专业学术著作读者不多,特别是佛教的专业术语非常难,就算是专家,因为身处不同的研究领域,对有些文献的解读都很困难。这样的著作,对普通读者而言,是非常难读懂的。但我们写的“文库本”或者写给一般读者的知识类书籍,并不是把这些专业书籍通俗化,而是把专业领域所积累的成果放置到一个更大的视野或者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去,试图把握全景,阐释其中的意义,重新选择一个观察问题的宽泛度,然后从这个新的角度来切入写作。所以,并不是专业书籍的语言通俗化,而是写作视角上的转变。对研究者来说,这种视野的改变、问题的重新把握、研究范围的调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来确认这样的研究,它的意义究竟何在。而且我们写了这样的书,也能从读者那里得到很多的反馈,促使我对这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重新进行思考。这和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进行非常专业的研究,然后和很少的专业研究者进行讨论与深化,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工作方式。
特此感谢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艾菁老师的现场翻译及审阅文稿
(访谈载2016年6月19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原标题为《末木文美士谈日本佛教研究》。)
 打印本文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