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印本文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关闭窗口 日本人为什么用汉字来翻译西方概念

传入日本并经抄绘、上色的《坤舆万国全图》,1708年出版。底本是明末李之藻翻译的利玛窦1584版单色地图
现代汉语受日语外来词的影响很大,诸如“历史”“政治”“干部”“事业”“社会主义”这些人们今天司空见惯的词语,都来自于日语,有人甚至说“离开了日语外来词,中国人就不会说话了”。诚然,日本新名词很大程度上重建了中国这个千年古国的名词系统,但有人往往忽视汉语新名词的多元来源,以致只要看到双字词,就以为是从日本引进的。事实上,早于日本新词传入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华制新汉语”,当今日常用语中的很大一部分词汇由此形成。
马礼逊发愤编字典
在19世纪之前,汉语对西方词汇的吸收基本遵循这样一个模式:由来华传教士在中国人帮助下将一本西洋著作翻译为中文,因此书中的西洋专有名词有了中文的对应词汇。这种吸收模式与明代之前并无二致,见一个词,翻译一个词,不成体系。19世纪初,英国伦敦会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则将这种模式推进了一大步,在西方词汇和汉语词汇之间开始建立系统性的对应关联。
马礼逊于1782年生于苏格兰,据说和发明蒸汽机车的史蒂芬逊还是童年玩伴。马礼逊很早就立志成为传教士,曾在伦敦和一位广东人容三德学习汉语。马礼逊实际学的很可能是粤语,水平也未见得高,但已经是英国教会中汉语基础不错的人选了,因此被派往万里之外的东方。他是第一个来到中国大陆的新教传教士。

版画,1839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右)与他的中国助手。马礼逊在1815年至1823年间编了一部《中文字典》,这是最早的汉英字典
1807年9月,马礼逊初来中国,在澳门落脚。刚一登岸,马礼逊就感到了这片土地上浓厚的敌意。不仅因为汉字自身极不友好的天书级难度,当时清廷禁止中国人教外国人中文,还有一个今人看来很意外的原因,那就是葡萄牙人的阻挠。既得利益的葡萄牙天主教徒才不管你英国的基督教徒是不是上帝子民,人家本身就看你新教异端不顺眼,早个几百年把你们送上火刑架都有可能,更何况你们还有可能来抢生意。所以,没在澳门待几天,马礼逊就被葡萄牙当局驱逐出境,悻悻地来到了广州。
他一个高鼻深目的白人,广州城自然是明令禁止涉足的,好在广州城外的十三行有外国商人的货栈和居住区,他在这里找到了新的住处,也终于找到一位中国的天主教徒袁光明来教自己这个基督教传教士汉语。因当时中国禁教,为了偷偷传教,马礼逊迫切希望融入中国百姓生活,他像几百年前的利玛窦那样,穿着长衫布鞋招摇过市,学着用筷子吃粤菜,甚至开始留起了长指甲和小辫子,非常卖力地模仿着他心目中的中国人形象。这么做不但没有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反而更扎眼了。广州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口岸,老百姓对西方人很熟悉,西装革履早已习以为常,这副山寨打扮的洋人倒是第一次见,马礼逊不出意外地惨遭群嘲,说好的秘密传教也传不成了。此外,他不懂中国的书籍,只好托中国仆人去买,于是又毫无意外地被贪心的仆人坑了钱。
不过到1808年6月返回澳门时,饱受摧残的马礼逊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粤语和官话。马礼逊回忆起自己学习中文的曲折经历,感慨万千。不会中文,根本无法传教。既然自己已经兼通英语、粤语和官话,何不编一部双语字典,这样他的同胞学习中文就更容易了,他那种可笑的试错过程也不必再度上演。
耿直的人一般都很有毅力,认定了就不回头。马礼逊自1808年开始,以《康熙字典》为据,历经15年编成了三部分六卷本的《华英字典》(Dictionaryof the Chinese Language)。这部字典包含一部汉英字典和一部英汉字典,几乎是马礼逊一人独立完成。从此以后,来华的美、英新教传教士几乎都以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作为学习汉语汉字的经典教科书。在撰写过程中,身在澳门的马礼逊迎来了他的苏格兰老乡米怜(WilliamMilne),令孤军奋战的马礼逊十分欣慰。几年以后,米怜在马礼逊的建议之下前往华侨聚居的南洋马六甲开辟传教事业,临行前带上了马礼逊推荐的刻印匠人梁发。这个梁发多年以后写了一本叫《劝世良言》的传教手册,让一位叫洪火秀的落第士人大受启发,于是当即改名秀全,接下来的故事,想必读者们一定很熟悉。

《康熙字典》,清康熙年间,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
马礼逊《字典》的意义究竟何在?冯天瑜教授曾列举过马礼逊《字典》的几个词条,其影响力之大,一看便知:apostle使徒,black lead Pencil铅笔,Christ基利斯督,Critic of books善批评书,digest消化,ex-change交换,judge审判,law法律,level水准,medicine医学,natural自然的,necessarily必要,news新闻,novel a small tale小说书,organ风琴,practice演习,radius半径线,spirit精神,unit单位等。若不是马礼逊近几年被学界关注,其中很大一部分词汇肯定会被想当然地当作日本人的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清末民初《泰晤士报》派驻北京的著名记者莫理循和这位马礼逊同姓。来华不久,莫理循发现,许多英国人在报上看到发自中国、署名Morrison的稿件,竟惊呼80多年前的那位传教士马礼逊还健在,令这位年轻人哭笑不得。这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对当年的英国人而言,马礼逊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代言人。
科学名词翻译与近代中文报刊
马礼逊之后,传教士的造词事业兴继不绝。许多图书馆藏有再版的马礼逊《华英字典》,其扉页下半部分往往会有“The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的字样。懂行的人一眼便知,这是一个大名鼎鼎的机构——墨海书馆。这是上海最早的一个现代出版社,为上海最早采用西式汉文铅印活字印刷术的印刷机构,至今国内的出版印刷界的行业史志撰写过程中都绕不过墨海书馆。

马礼逊《华英字典》(卷3)影印版,2010年大象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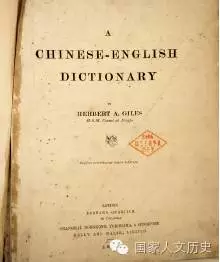
翟理斯《华英字典》1892年版,由上海别发洋行发行
墨海书馆的创办人叫麦都思,此前在马礼逊的老朋友米怜那里学中文。米怜当时在马六甲编纂了一份中文小刊物,麦都思也经常在上面写文章,主要内容当然是传教士的劝善信教的老本行,但也有一些新闻内容。这份报纸叫《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现在被奉为“以中文出版的第一种现代报刊”,其实当时不过是一份发行量几千份的免费小册子,近代的中文新闻报刊事业竟就此发端。
1843年,上海开埠不久,麦都思和几个传教士来到上海,在当时的江海北关附近伦敦传道会总部开办了墨海书馆,即如今的黄浦区福州路一代,现在仍然是书店密布的文化宝地。书馆用一台牛力驱动的铅字印刷机印制圣经等书籍。洋务先驱郭嵩焘称呼麦都思为“墨海老人”,有人认为“墨海”就是麦都思(Medhurst)的音译,不过更多的人说是取“翰墨海洋”之意,透着一股雅意。
麦都思还曾外出考察,他也像马礼逊一样乔装打扮,剃光前额头发,安上假辫子,戴上墨晶眼镜,身穿长衫,头戴瓜皮帽,走访江浙桑蚕和茶叶产地。这既说明这些传教士对中国抱有一种真切的好奇之心,也反映出中国老百姓对外国人的陌生与不适应,如果说清代上层士大夫对西学多少还有一点微弱传承的话,那老百姓对洋人可真是完全的陌生了。
墨海书院先后出版了《数学启蒙》《续几何原本》《代数学》《代微积拾级》等令作为文科生的笔者无言以对的著作。这些著作的主要翻译者均为伟烈亚力。伟烈亚力厘定了“圆锥”“曲线”“轴线”等几何术语,还首次向中国介绍了虚数,并引入了×÷=∵∴∞等西方运算符号。 “代数”“微分”“积分”“系数”“椭圆”“级数”“常数”“变数”等词,为当代学生创造了无尽的挂科可能。

绘画,左为麦都思,英国传教士,自号“墨海老人”,先后印行了30 余种中文书籍
这些酷爱新闻出版事业的英国传教士注定是闲不住的。麦都思于1853年来到香港,想起此前的办报经历,又搞了个叫《遐迩贯珍》的刊物,看名字很像某种神秘的宫廷御膳,其实是中国本土出现的第一个中文期刊,内容上也越来越世俗化,后来都开始登广告了。此后不久,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也创办了刊物《六合丛谈》,这是当时中文世界最好的综合性新闻刊物。其他刊物往往都是西方传教士劝人信教的,这部刊物虽不能免俗,但却以“通中外之情,载远近之事,尽古今之变”为旨趣,刊登了大量世俗的国内外消息,其影响力远迈中国之境,尤其受到日本追捧。下面的一个故事就和《六合丛谈》的东传有直接关系。
《六和丛谈》,1857年(咸丰七年)在上海出版,封面书“江苏松江上海墨海书馆印”
汉语新词给日本人打开世界之窗
日剧《神探伽利略》中,主角汤川学的黑板上常常满是物理、化学名词,中国观众看到往往觉得很熟悉,因为许多都是汉字词。“化学”是不折不扣的新名词,清末之前从未见于汉文典籍,不仅中国典籍没有,日本典籍也没有。“化学”一词的发明权,长期被理所当然地归功于日本人,毕竟人家科技先进嘛,科技词汇想必是人家发明的。但“化学”这个现在为中日两国所通用的名词,其诞生地是上海,创制过程中也有中国人的身影。
日本兰学(日本对西学的称呼)著作将荷兰语化学一词Chemie音译为“舍密”,看上去似乎有一种诡异的玄学色彩。此前,马礼逊《华英字典》可能是看化学家也把瓶瓶罐罐放到火上炼烤,于是将chemist(化学家)一词生硬地翻译为“丹家”,即炼丹药的方士。
20世纪80年代,新成果不断涌现,特别是著名的改良派思想家王韬的日记受到学界瞩目。人们惊讶地发现,王韬于1855年在日记中记载自己观看一位“戴君”表演实验的经历。面对戴君“特出奇器,盛水于桮交相注,渴顿复变色”的现象,王韬恍然大悟,就把这种神奇的把戏“名曰化学”!这一记录早于已知的所有日文文献。
经过旅日学者沈国威的考证,这位戴君并不姓戴,而是一位中文名叫戴德生的英国传教士JamesHudson Taylor。关于“化学”这两个字究竟是王韬还是戴德生提出,学界有争议,当年戴德生的汉语水平相当一般,似乎达不到自创新词的程度,故还是王韬发明的可能性更高一些。沈国威教授发现,这次戴德生在王韬面前表现的化学秀不仅仅标志着“化学”这个名词的诞生,更与“化学”这个译名日后东传日本有直接关系。
原来,王韬当年的正式职业是上海墨海书馆的雇员。王韬对“化学”这个译名甚是得意,转口告诉了书馆的传教士伟烈亚力。结果伟烈亚力也觉得不错,于是在墨海书馆出版的《六合丛谈》中沿用了这种译法。
《黄浦帆樯》,清末张志瀛绘。描绘王韬拜访上海墨海书馆和黄浦江上的轮船。出自清末王韬《漫游随录图记》
明清两代,汉语文言是东亚世界通用的书写语言,汉字是东亚世界的通用文字。不仅中国使用,日本、朝鲜、琉球、越南等国的知识分子都以汉字作为主要书写手段。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孙中山在会见日本社会活动家宫崎寅藏、越南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潘佩珠,蒋介石会见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金九,双方都是通过书写汉字“笔谈”来实现交流的。当时的东亚知识界因此拥有了极高的流动性。
1859年,日本德川幕府将原本不多的宗教内容删去后,以官方名义出版了《六合丛谈》的合订本,让日本人第一次见到了“化学”一词。日本兰学界早对莫名其妙的“舍密”大为不满,一看这两个字非常兴奋。仅仅在《六合丛谈》传入日本一年后,兰学家川本幸民的《万有化学》就一口气删掉了所有的“舍密”,全部改为“化学”,此后经学校教育的普及,化学一词逐渐为日本人所接受,以致完全记不得自己原创的什么“舍密”了。就这样,诞生于中国的“化学”一步步传到了日本。
19世纪中叶,日语的词汇不仅尚未能影响汉语,反而是汉语的新词向日本输出,给幕府末年的维新人士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日本人大量造词,要到19世纪60年代的明治时期。至于日本的所谓“和制汉语”新名词对汉语词汇系统的渗透则要到甲午战争以后了。
世界潮流摆在那里,中国人迟早都会形成一套新的词汇体系去描述这个科学昌明的新世界,中国的孩子们也迟早得接受中文版数理化试题的折磨。现在的日语面对新概念时,基本已经停止新“和制汉语”的创造,而改用假名音译,明末徐光启、利玛窦等先贤开创的华制新汉语至今仍然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新的词汇几乎每天都在涌现,这就中国人语言创造力的明证。(文/罗山)
(参考文献:沈国威:《译名“化学”的诞生》,《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1期;刘广定:《“化学”译名与戴德生无关考》,《自然科学史研究》,2004年第4期;冯天瑜:《晚清入华新教传教士译业述评》,《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湛晓白、黄兴涛:《清代初中期西学影响经学问题研究述评》,《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第1期)
转自“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公众号(gjrwls),腾讯文化合作媒体,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打印本文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关闭窗口